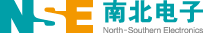近年来,得益于方法学的重大进步和从分子到整个大脑多层次的数字数据集成及建模,脑科学研究无疑已迈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神经科学与技术、计算的交叉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新兴的大脑科学整合了高质量的研究、多层次数据的集成、跨学科的大规模合作文化,同时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就如欧洲的“人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 HBP)所提倡的那样,采取系统化的方法对于应对未来十年内的医学与技术挑战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为未来十年的数字大脑研究发展一套新概念,并与研究社区展开讨论,寻找共识点,以此确立科学的共同目标。同时,提供一个科学框架,支持当前及未来的EBRAINS研究基础设施发展(EBRAINS是HBP工作产生的研究基础设施)。
此外,本文还旨在向利益相关者、资助组织和研究机构传达未来数字大脑研究的信息,吸引他们的参与;探讨综合性大脑模型在人工智能,包括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面的变革潜力;并概述一个包含反思、对话及社会参与的协作研究方法,以应对伦理与社会的机会与挑战,作为未来神经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为论文上篇)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对人脑的理解已取得显著进展。面对大脑复杂性的挑战,研究者已经从单一分子和基因的层面,到突触、细胞和局部神经回路,乃至于作为一个整体器官的大脑的各个层面,探索其多种功能和功能障碍。
今天,神经系统疾病已成为继心脏病之后的第二大死亡原因,造成约2.76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Feigin et al., 2019)。[1]2010年,欧洲的大脑疾病总成本高达 7980亿欧元(Olesen et al., 2012)。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并开发更有效的因果治疗方法,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器官的复杂性和其庞大的规模,同时也存在合法的伦理和方限制,这些限制不允许我们直接从材料中获取所有必要的数据集。这为实证和数字研究带来了挑战。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洞察大脑的基础结构、器官中的生理现象,以及对神经机制的理论理解。
结合结构性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磁图(MEG)或脑电图(EEG)等多种方法,科学家们已成功识别与感觉、运动控制和执行功能相关的生物标志。然而,要从细胞机制到系统层面的效应建立联系,我们需要多尺度神经科学的支持。还有研究指出,我们还需要理解大脑各区域之间是如何进行“语义”交流的(Douglas & Martin, 2007)。例如,Buzsáki(2019)认为,全局和局部的振荡构成了大脑内部通信的“语法”。
针对多种脑疾病,遗传机制的明确已对诊断和治疗起到了直接的重要作用。此外,几种信号传导途径的分子和细胞机制也已被解码。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加深对大脑组织、大脑结构与功能、动力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其在学习和睡眠期间的重组,以及认知基础的条件。模拟以及人工智能解析意识结构的潜力已成为神经科学讨论的一部分(见 Dehaene et al., 2017; Graziano, 2019)。具备模拟意识能力的机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意识的困难问题”可以通过模拟“意识的容易问题”来解决(Chalmers, 1995)。
大脑的多尺度架构不仅赋予了它适应能力和计算能力,也促成了不同大脑区域间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的程度取决于不同大脑区域和其他因素(Croxson et al., 2018; Zilles & Amunts, 2013)。理解这些变异将有助于改进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同时促进对认知功能机制的阐释。从基础科学的角度看,这是理解进化和不同认知特征的必要条件(Thiebaut de Schotten & Forkel, 2022)。
神经成像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光学方法的创新进展,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大脑功能的了解。这些技术提供了更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并能持续观测更长时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他们提供了大量数据集,尽管这些数据集的分辨率较低。这些数据帮助我们识别了决定大脑健康与衰老的多种因素,例如生活方式、环境因素、基因构成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实证研究产生了大量高度结构化的数据以及元数据,也加剧了对日益增长的对数据集的需求。
那么,根据目前的数据,哪些问题已经可以得到解答,哪些地方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呢?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悉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在其获奖演讲“大自然给科学的礼物”(Brenner,2003)中提到:“我们正在数据的海洋中挣扎,渴望获得知识。生物科学的爆炸性增长得益于我们积累描述性事实的前所未有的能力……我们需要将数据转化为知识,并需要一个框架来实现这一转换。”
尽管现有大量数据,但各实验室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差异巨大,数据往往无法直接比较。此外,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来源追踪的数据,包括具有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功能成像数据及组学数据等,还相对稀少。
这些数据往往来自多个不同的实验室。显然,要定义和实现宏伟的科学目标,需要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实验室之间,以及拥有互补技术专长的实验室之间的紧密合作。例如,需要图像分析、神经解剖学、数据分析、计算、生理学、生物医学、建模、理论和计算的专家共同协作。研究大脑和大脑疾病时,一些神经伦理问题和社会需求与价值的考量也非常重要,这促使神经科学家与人文科学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总的来说,这些发展促进了跨学科合作,需要适当组织和重视。
这种横跨不同大脑研究领域的紧密合作是HBP等大型国际项目的显著特点。[2]HBP从2013年启动至2023年结束,是欧洲未来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旗舰项目之一。HBP项目的启动目标是深入理解大脑,这一目标与当时计算和数字技术的显著进步相符(Amunts et al., 2016, 2019; Markram et al., 2011)。HBP是全球首批大规模大脑研究项目之一,在将数字大脑研究转变为一个更方便协作、可复制、以及伦理和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学科方面发挥了开创性作用(Amunts et al.,2022)。
神经科学社区现在已经能够利用最新的计算、模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项目中创建的实验数据、计算模型和工具、仪器以及如神经形态系统这样的专用硬件,旨在显著加速大脑医学和研究的发展,并为半导体行业提供低能耗解决方案(“大数据需要硬件”,2018)。该联盟已经开发出EBRAINS这一协作研究平台,目标是通过数字工具和计算技术将大脑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进一步发展医学和神经启发型技术的应用。
EBRAINS已成为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ESFRI)路线图的一部分,ESFRI的目标是支持欧洲研究基础设施政策的连贯和战略导向的方法,并促进多边倡议,以更好地使用和发展研究基础设施,这不仅涵盖欧洲,还扩展到跨层面。EBRAINS正在被开发成为一个由科学家为科学家服务的可持续研究基础设施。
为应对伦理与社会问题,HBP在EBRAINS的治理和研究层面融入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的原则和实践。其目标是预测、反思,并在网络层面采取行动,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神经伦理、哲学、社会和法律挑战,并主动解决有关EBRAINS研究及其成果的关注、滥用和商业化的双重用途研究问题(Stahl et al., 2021)。
展望未来十年,我们基于已取得的成就,确定了对大脑知识的缺口,并制定了未来的研究目标。我们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将从数字大脑研究的进展以及技术与计算交叉领域的最新发展中受益。数字大脑研究利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计算、建模和模拟、图谱等领域的优势,推动大脑研究进展,并将其转化应用于医学和技术。这些目标也将从神经科学与神经伦理的整合以及涉及需求、可接受性和期望性的伦理与社会问题的多学科合作中获益。
本手稿通过一个参与性过程发展而来(附录1)。这项工作由HBP发起,邀请整个研究社区通过提交评论共同塑造愿景。这个过程持续超过两年,使得原始文件经历了实质性的变更,研究概念得到更广泛的代表,有时还伴随着争议性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建模和模拟的角色。作者们就共同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达成了共识。虽然我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万能”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确信,围绕数字大脑研究主题的讨论将推动更广泛的神经科学领域的进展(见附录2)。

Rafael Yuste:“作为在美国工作的欧洲人,我强烈支持这一倡议,它有助于将欧洲神经科学推向领导地位,并帮助欧洲国家利用共同努力实现相同目标的好处。”
Linda Richards:“总体而言,这份手稿呈现了推动该领域前进的新方法,非常令人兴奋。”
Alexandra A. de Sousa:“作为欧洲脑进化研究网络的创始人,我强烈支持这一倡议,特别是它提到了比较和进化神经科学的重要性。”
蒲慕明说:“理解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并开发有效的诊断和干预脑疾病的方法,是所有社会的长期目标。这些任务庞大,需要全球合作,以促进快速进展并共享知识与技术。中国脑科学项目现已由中国政府全额资助,为未来十年提供保障。许多中国科学家与欧美科学家有密切联系,他们希望建立国际合作项目,并设立有效的协作机制。”
George Paxinos:“观察到在多层次脑图谱的开发中取得的进展,实在令人兴奋。近年来出现的高级数字工具为研究不同物种的大脑结构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为了理解我们的缺失部分并激励我们的数字大脑研究方法,回顾现代神经科学的起点至关重要。这一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多个关键阶段。
现代神经科学起源于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大脑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被视为结构单一的整体,转变为一个由众多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网络(DeFelipe, 2009; Mazzarello, 2010; Shepherd, 2015)。
20 世纪初关于大脑分区的新概念,即大脑中负责特定功能的区域,催生了微观结构的大脑图谱的诞生(例如,Brodmann, 1909; Vogt & Vogt, 1919)。系统的神经病理学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健康和疾病状态下大脑的理解。1930 年代全脑电图为 1950 年代细胞内电生理记录以及对神经元和突触生理学的基本了解铺平了道路。1930 年代化学神经传递的发现及1950 年代药理学的对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Carlsson et al., 1957; Dale et al., 1936; Vogt, 1954),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于大脑如何作为一个分布式计算网络灵活适应变化世界的基本理解(Dayan, 2012)。
1950年代引入的Hodgkin-Huxley模型用数学术语描述了动作电位的机制(Hodgkin & Huxley, 1952)。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关于感觉(主要是视觉)和运动系统的生理学及解剖学研。
亚洲城官方登录入口
上一篇:MAXHUB带着AI大模型“冲进”会议室 下一篇:ICLR 2024杰出论文出炉:“大模型”成最大赢